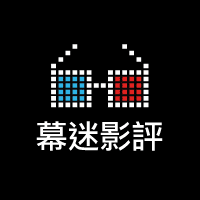知道香港電影《十年》是今年一月底香港電影金像獎甫公布入圍名單,《十年》與《五個小孩的校長》(關信輝)、《智取威虎山》(徐克)、《葉問3》(葉偉信)、《踏血尋梅》(翁子光)一起入圍 「最佳電影」這個項目。當時消息一出中國官方隨即開始放話、河蟹 ,甚至明文禁止中國媒體轉播金像獎頒獎典禮。記得看到這些新聞時我並沒有多想,只覺得這應該又是一部被放大檢視的小品電影,又覺得中共何必如此緊張?香港本土電影的影響力本來就已經越來越弱,是在怕什麼呀?(認真問)

之後在四月的頒獎典禮上,壓軸項目「最佳電影獎」的頒獎人赫然是本屆金像獎董事局主席爾冬陞(備註1),當他打開信封宣布本屆最佳電影是由《十年》奪得的時候,在電腦前面的我幾乎可以感受到全場觀禮嘉賓在不同的座位區域有不同的反應,這歡欣有之、驚愕有之、振奮有之甚至憤怒有之的情緒分隔,就像我們在挑演唱會座位一樣,前十排是紅色搖滾區、中間是藍色座位區、二樓是便宜的看台區 。 如此涇渭分明的情緒反應,竟然比電影本身更令我想要探究,尤其是寰亞電影老闆林建岳以及電影投資人身兼資深演員黃百鳴的猛力砲轟反而挑起我的看片慾望。當然當時內心也有一陣焦慮狐疑:難道電影本身Quality真的有問題嗎?難道這真的是政治意識凌駕了藝術嗎?

看了電影之後,發現我的政治焦慮太過於膚淺了。
或許你會問:除了政治,《十年》這部電影還可以談什麼?我想就先從林建岳與黃百鳴的怒火說起吧。黃百鳴發言的大意是「影片成本低、沒有提名其他單個項目代表製作技術不完備、以後我也要來拍尖銳題材就可以得獎」,其實要反駁黃百鳴這套說法有很多種方法,例如「低製作成本」這點就有網民找到1998年陳果導演的《香港製造》製作經費同樣為50萬港幣,同樣也榮獲當年金像獎的最佳電影獎。但我比較注意的是黃百鳴的的言下之意,他認為這種結果「對認真去做電影的投資者並不公平」。而林建岳的說法更是淺顯易懂,他說「假如我跟你說,有一間餛飩麵店是全香港最好的餐廳,你會不會服氣?一個新的導演,第一部戲會好過徐克嗎?可能你說見仁見智,但對我來說,我不承認。」

在此我們先假設這兩位前輩是為了「健全香港電影工業」而發聲,發言不僅無關(討好某方的)政治立場,反而是不希望政治影響香港電影,那麼他們覺得好的電影是什麼?
綜合他們的說詞,看起來他們似乎覺得一部好電影必須要有「精緻的場景布置」、「細膩的燈光設計」、「出色的攝影構圖」、「高雅的服裝美術」、「成熟的演員演技」,換言之,他們認為形式上的「美」或「完備」才是一部好的電影。
可是我們為什麼喜歡《開心鬼》?我們為什麼喜歡《家有喜事》、《最佳拍檔》?為什麼《富貴逼人》系列、《表姐你好》系列、《省港奇兵》系列會如此受歡迎的拍了好幾集?我認為我們之所以喜歡這些電影,不是它們有完備的形式,而是因為我們喜歡這些電影裡呈現的世界,我們一看再看,看到最後已經搞不清楚到底是我們看著電影長大還是電影看著我們長大。這是黃百鳴後來製作的合拍片《家有喜事2009》、《花田囍事2010》、《八星抱喜》做不到的。對香港觀眾、香港電影金像獎來說《五個小孩的校長》、《智取威虎山》、《葉問3》可能也做不到…

法國藝術評論家尼可拉斯.柏瑞歐(Nicolas Bourriaud)曾說『通常我們會將形式定義為週邊輪廓而不是其中的內容。然而現代美學說到"形式的美"(Beauté Formelle)其實是自行創造出了一種形式(forme)與背景(fond)的對等性,將形式與背景混合(或者說是混淆)了。我們根據藝術品的造型形式(forme plastique)來評價一件作品;對於最新的藝術實踐,最流行的評論是拒絕賦予這些實踐以"形式上的有效性"(éfficacité formelle )的,或者往往指出這些實踐在"形式上的解決"(résolution formelle)方面有所欠缺。觀察當代藝術實踐,在"形式"之外,我們應該談的還有"形成"(formation):某個物件(藝術品)在一種風格或是一個署名的介入之下便自我封閉了,而當下活躍的藝術則相反——只有在會面時,在藝術命題與無論是否具有藝術性的其他資訊之間產生交談的關係中,這些藝術才會呈現出其形式。』(《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來源)

我想《十年》之所以以50萬港幣的成本達到600萬港幣的票房成績;之所以奪得金像獎最佳電影;之所以被認同是藝術,正是因為它在「與其他資訊之間產生交談的關係中(抨擊、河蟹、禁播),『形成』它的藝術形式」。這關係是林建岳所言「部分評審對電影的認同超越單純藝術和技術」;是詩人兼影評人廖偉棠所言「金像獎頒發『最佳電影』予《十年》是犧牲了藝術」;是環球時報所言「電影是嚇唬香港社會的思想病毒」。換句話說,中共、環球時報、林建岳、黃百鳴等人是讓《十年》的藝術形式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啊!

台北電影節在7月9號辦了一場「《十年》電影焦點對談講座」,邀請五位導演以及作家平路女士與觀眾對談。會中我舉手問了個(應該不是很禮貌的)問題:「這樣的議題香港一些導演如杜琪峰、陳果都討論過,只是他們用的方式都是隱喻隱喻再隱喻,為什麼《十年》要用這麼直白的方式來表達,這讓電影不像藝術作品比較像是社會工具?」《自焚者》的導演周冠威回答「我想要直白,所以我比TVB更TVB,我不知道你如何定義藝術,但我想強烈直接,如果你看到一個小朋友要快被撞,你不會跟他說馬路如虎口,而是直接把他拉出危險!現在的香港已危險到需要如此發洩出來,我不會說這是最好,但我希望能夠看得明白、清楚,這也是藝術的綜合。」
關於直白的部分,如果這個回答是在「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之前,或許還不能說服我,但眼睜睜看著共產黨違反50年不變一國兩制的承諾跑到香港抓人、採取恐怖手段要拿到購書人的資料,不得不承認導演說的很正確:「現在的香港已危險到需要如此(直接的)發洩出來!」

另外,我也認為對於批評者所要求的藝術價值《十年》並非不能而是不為。
誠如大家所知,構成《十年》的五部短片分別是郭臻導演的《浮瓜》、黃飛鵬導演的《冬蟬》、歐文傑導演的《方言》、周冠威導演的《自焚者》、伍嘉良導演的《本地蛋》。
開場短片《浮瓜》的導演郭臻其實早在2010年(他的作品)就跟台北電影節的觀眾見過面了。那年策展人選了同樣是短片集合的《香港四重奏》進入「亞洲大不同 Voices from Asia」的單元中,原本四重奏分別是為羅卓瑤的《赤地》、邱禮濤的《生炒糯米飯》、麥曦茵的《偏偏》 以及陳果的《黃色拖鞋》。不過後來羅卓瑤的《赤地》因故取消(據說是要到別的影展搶世界首映),改由郭臻的學生畢業作品《媽媽離家上班去》代打。當時我很好奇什麼樣的學生作品能與邱禮濤、陳果的作品並列,看過之後我給這部作品很高的評價,不僅僅是內容上外籍保母的劇情很能引起港台觀眾的共鳴,而在製作技術上,郭臻的畢業作跟兩位大師比起來沒有遜色之處。
而根據維基百科資料,《自焚者》的導演周冠威在2013年的第一部劇情長片《這是一個複雜的故事》是由九位香港演藝學院學生共同創作,周冠威以外其他八位同學負責攝影、錄音、剪接、後期製作等工作,是少數能夠在院線正式放映的學生作品。台灣的電影台曾經播過這部電影,雖然未臻完美,但算是一部合格之作。
另外可能很多人也發現到,《方言》的導演歐文傑也是杜琪峰銀河映像20周年紀念大作《樹大招風》的三位導演之一,《樹大招風》之好看,我可以給他99分!
舉這三個例子只是要說明,我覺得導演們並不是沒有能力做得更美、更好,不過就如《冬蟬》的導演黃飛鵬說:「我們拍《十年》,這或許是逼出來的,因為資源有限而用短片組合與想像來做,這些都是迫在眉睫的情況。」我覺得他們其實可以等,等到更多的資金、更多的奧援、更成熟的時機,可是《十年》連香港電影發展基金(類似台灣的輔導金)都來不及申請(申請時程需約半年以上),選擇以50萬港幣為總製作費(等於平均一部短片的成本是10萬港幣/40萬台幣)來拍攝。或許,五位導演在一開始就放棄追求那種工整的形式、完備的美學吧!

這也讓我想到葡萄牙當代最重要的電影導演之一Pedro Costa曾說過他已經不想再拍電影,因為他發現花了那麼多錢、費了那麼多人力拍出美美的電影,但美美的電影並沒有改變什麼,這世界還是有90%的人生活在苦難中。(2015年台北電影節映後座談語)
我們應該慶幸,連同這五位導演在內,還有許多人沒有對電影失望,依然想要透過螢幕對這個世界有話可說。
當然,你可以說「Un cinéphile est quelqu'un qui attend trop de choses du cinéma.」(所謂的影迷就是對電影有太多的期待~Serge•Daney),你也可以討厭這種政治主題先行的電影,但我認為現代政治過程經過常態化之後(從不能講到可以私下小聲講到可以對不特定的大眾講),以及國家政治所建構經濟體系所涵蓋的範圍越來越廣泛時,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已經是一個絕對的狀態。換句話說,現代人每天的生活都脫離已經不了「政治」,如果你不希望意識形態滲入藝術當中,那你必須比其他人保持更高的警覺,警覺在你生活的日常中,滲進你的思想的是什麼?

下文劇情心得
《十年》五部短片中,最淺顯易懂得應該是歐文傑導演的《方言》,劇情描述10年後的香港,廣東話已經被邊緣化(其實現在中共已經將廣東話貶抑為「方言」),普通話成為主流。劇中主角是一名計程車司機,因為沒有通過普通話的考試,被政府規定只能在有限的區域載客,不僅影響生計還失去尊嚴。相信許多逮丸同胞看到這一段都心有戚戚焉吧,當年在學校講台語要被檢舉、被罰錢的暗黑回憶浮上心頭…歐文傑導演在座談會上說,他並不是要排擠中文,而是想守護廣東話。老實說,看到現在台灣的小學開設方言課,我內心常常只有一陣悲涼,台語被國民黨用政權的力量消滅殆盡後,我不認為它能在一周幾小時的課堂上得到新生。語言是活著且不斷變化的,從前強調說台語(或說台灣國語)是沒水準;現今強調"台語之美",就我個人觀點這兩者都不是正常的現象,能用這個語言好好表達自己的觀點,才是最重要的。但曾以學講廣東話為樂的我,確實沒料到有一天香港的小學生會說出「喔~你說廣東話~我要告訴老師!!」…
跟《方言》比較起來《自焚者》的劇情則是稍稍複雜一點,尤其對海外的觀眾來說,所以如果我的理解有誤歡迎指證。除了暗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類似台灣之前的刑法100條-專治內亂罪),並辯證香港的未來是要維持一國兩治、要求英國協助或者直接港獨。也藉由影片不同年輕人的立場去思索和平抗爭與激烈手段是否是完全對立的行動方式。《自焚者》雖然用的是偽紀錄片的形式在講故事,但影像表現充滿詩意,而且當中牽涉複雜的時代背景(「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也讓電影在直白外多了討論空間。

至於郭臻的《浮瓜》則是講述中共當權者為了在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其實應該就是上述的「基本法第23條」),利用黑社會小嘍囉自導自演一樁槍擊案,希望藉此恫嚇香港市民達到立峻法的目地(諷刺的是其手法跟環球時報批評《十年》是的內容一樣的)。我覺得《浮瓜》讓人驚艷的是導演對政治陰暗手段的想像力:黑吃黑、製造主要敵人、欺騙次要敵人、政客自導自演、假戲真作、真戲假作,尤其是襲擊行動前那些人五人六的政黨領袖為了誰被殺而起糾紛,每個人都希望是"本黨"的議員被槍擊,藉此拿選票、求版面,老實說我一直覺得像台灣這種被政黨政治耍了10幾年的人才會暸這個,想不到香港人會有這種黑色幽默的想像力。

《本地蛋》是最後一個故事,主角是我都稱他為三叔的廖啟智(他在《無間道2》裡吹口琴的模樣印象很深刻)。三叔在影片中飾演一個雜貨店老闆,隨著政府的嚴苛政策,香港本土產業日漸緊縮,就連雜貨店賣的蛋不能寫上「本地」兩個字,以致香港最後一間養雞場決定結束營業前往「台灣」找退路。小糾察隊除了在街上查看有沒有違禁用詞,也會跑到書店視察有無租售禁書。說真的,這部短片原本因為小糾察隊就是紅衛兵這個比喻太明顯而會顯得太荒謬,但好巧不巧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結果電影反會像郭臻導演在座談會說的「我們預設的情況已經陸續在發生了,可能是我們想像力不夠吧,沒想到更誇張的內容。」

黃飛鵬導演的《冬蟬》是這五部裡風格最為特殊的一部,在喜歡「直接電影」的香港,似乎被戲稱是最多人看過的實驗電影。事後找資料才知道,電影所要描述的,不只是我以為的歷史、記憶與保存之間形而上的關係(想到陳界仁),導演黃飛鵬本人參與馬屎埔村護村運動多年(可類比台灣大埔事件),所以《冬蟬》要表達的好像是更實際的更具體但也是更悲觀的理念: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失去很多,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這些東西變成標本。
兩年前受一位關心環境議題的朋友的邀請,我跟她曾到馬屎埔村以及馬寶寶農場走馬看花了一個上午,還很應景的在香港戲院看了《竊聽風雲3》(講新界土地徵收的利益糾紛)。後來又在紀錄片《未夠秤》裡看到主角之一不到18歲的馬雲祺常年參與反高鐵運動,孤陋寡聞的我才知道,香港不只是我以為的金融中心,他如今面對的新舊問題、發展與保留問題、經濟與環保的問題,種種矛盾根本跟台灣就是照鏡子。
《冬蟬》的節奏雖然稍有拖沓,但主題思考不同於其他四部影片,且影像構圖具有詩意,也許再看一次會有更多的感受。我喜歡男主角決定把自己變成標本的設定,如果你不想被改變,只有永久的保留現在的自己。

這五位導演拍完這部電影後,創作生涯我想應該多少會有點改變。意料中的就是往後新的企劃都會遇到阻礙,投資人或片商可能會礙於中共而卻步。但我猜也有投資人拿著錢來,要他們拍20年、30年、50年…無論是哪一種改變,都會是一種扼殺。只希望這樣的情況不要太多、也不要太久,也期待能看到更多不同屬性的作品。
最後用我偶像杜琪峰的話當結尾:「問題不是他們(導演),是這個世界是這樣,才讓他們有機會這樣講…」

備註:爾冬陞他說不是因為自己是主席想出風頭,是找不到人擔任頒獎人,因為大家都怕打開信封,真的是「十…」開頭的電影。他又說,一個寫頒獎典禮腳本的年輕人問他「腳本裡可以出現"十年"這個詞嗎?」然後他回答「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我個人覺得他說完話之後底下一陣尷尬..
後記1:我在台北電影節座談會上問的問題好像有點不禮貌,但沒有要嗆聲的意思….(已流淚)
而且其實我真正想要問的問題沒問到(´・ω・`)…
我想問導演們,拍過這《十年》後,對「電影」(Cinema)的態度有沒有改變?希望有人認識導演的話可以幫我轉達一下π_π
還有《浮瓜》為什麼要叫「浮瓜」?
後記2:我尊重林建岳以及黃百鳴以及寰宇電影公司老闆林小明、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洪祖星等等所有對《十年》的批評,電影本就是很主觀的。但是,只是因為一次結果不滿意就發動更改金像獎賽制我就只能送你一句"你黐線"(發音:雷欺醒)
相關文章:
《香港三部曲》Fuck you very much
照片多數來源:《十年》官方粉絲團
故事劇情:8
氣氛營造:8
演技表現:8
題材鮮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