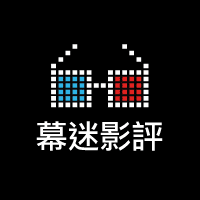每隔十二年,在喜馬拉雅山腳下的森林裡,戴著面具的群眾,從滿月到朔月,進行為期二週的修行。在這段時間內,不可暴露自己的性別、身分,也不可探聽他人的來歷,連話語都必須盡可能減省。一旦觸犯了戒律,面具就會被當眾拿下,以示毀滅與懲罰。失去身分、失去話語、既非生,亦非死,以這樣的日子為背景,《等待成一首歌》(Hema Hema: Sing Me a Song While I Wait)講述了一個第一次參加修行的年輕人,如何在修行過程中受到誘惑,進而犯下殺人罪行,在罪咎漫長的糾纏中,試圖尋找救贖的故事。全片在不丹美如明信片的深林中拍攝,濃綠的樹木、傳統的服飾、鮮豔的面具,交織成一則似遠實近的寓言,以及一個重新尋回自我的旅程。
《等待成一首歌》導演為執導過《高山上的世界盃》(Phörpa)的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Dzongsar Khyentse Rinpoche, Khyentse Norbu,或譯欽哲諾布),同時也是藏傳佛教的喇嘛。電影中充滿了宗教元素,無論神秘色彩濃厚的修行儀式、重複出現的梵語頌歌,或者刻意採用的藏曆紀年(水猴年、火猴年),無不予人神祕的疏離感。但在此形式底下,探討的仍是普遍的主題:身分、慾望、罪與罰,這些凡人都會面臨的課題。在幾乎不露臉的狀況下,演員只能透過肢體、眼神,甚至指尖傳達情感,卻能達到如主演Tshering Dorji在訪談中所形容:「So less, yet so much.」的飽滿境界。

電影中的長者一再強調「隱藏身分就是力量」,誠然,匿名的狀態使人彷彿與自己切割,戴上面具,隱藏在各種象徵性的人、獸、或者情緒後面,使人抽離當下的現實,不擁有身分,一切都能事不關己。但很快地,面具形成另一種身分,主角藉由面具辨認與自己調情的女人,而後也因面具的關係認錯人。人的臉孔被面具掩飾,但面具反過來隱喻人的面容。劇中,主角被分配到的是一個沒有表情的人臉面具(演員表上也是Expressionless),如這張臉所暗示,電影前半,他疏遠著縱慾的人群,僅透過簡單的手勢與人交流,甚至大多時候靠的是偷窺。與他調情的女人戴著紅色面具,代表了大膽與挑逗,而在被他錯認的女人身上,紅色面具又成了被強暴的血與怒。被他所殺的男人戴著安詳(Serene)的面具,似乎反過來暗示死亡的寧靜恆定。面具成了一個豐富的隱喻,既強化情緒又簡化情緒,既隱藏身分又創造身分。而當面具被摘下時,重重的隱喻散去,人必須直視自己的真面目。
隱藏身分是否就擁有自由?這也是電影中另一個核心命題,主角意外殺了人之後,主持修行的長者告訴騷動的群眾:「兇手的身分並不會被揭發,但他將活在罪惡之中。」這直接呼應到24年後主角重返這片中魔之地,承認自己犯下罪行且已經「瘋24年了」。罪與罰並不因匿名而取消,相反,為了贖罪主角必須拿下面具,電影並沒展示那必然痛苦的發瘋過程,最後對他與女兒間的關係也多有保留,但至少,他已面對殘酷的真相(無論自己身分的真相,或當年的悲劇的真相),贖罪的旅途也已展開。

在《等待成一首歌》中,「死亡」始終如影隨形,這裡的死亡非常具像,不只是夜間圍繞營火上演的戲中戲,還有為了被主角殺害的人辦的葬禮。那是一場哀傷而莊嚴的葬禮,在死亡與新生之間的間隙,也就是藏語中的Bardo(中陰),亡者被安置在舞台前方,主持葬禮的長者吟唱著:「你將沒有影子,沒有腳印。即使你找到回家的路,卻沒人會跟你說話,因為沒人看得見你。」死亡亦是一種身分的消除,即使掛念生者,卻已無法回頭,從頭到尾,亡者的面具都沒被摘下,似乎也暗示著,在死亡的國度,人人都沒有身分,人人也都平等。
除了試圖探討的主題外,片中的攝影、美術、燈光也都令人印象深刻,不丹的森林深邃廣袤,濃濃的綠意與鮮艷的面具形成強烈對比,視覺上非常美。劇組幾乎花了一年的時間製作面具、服裝,並浸泡、燻煙使其充滿年代感。此外,片中的夜戲在不使用人工照明的情況下,幾乎所有的光源皆來自火炬,影影綽綽,使圍繞著營火的吟誦、舞蹈,乃至指尖交纏、肉體誘惑,都帶著一種光影搖曳的美感。

原片名Hema Hema: Sing Me a Song While I Wait中的「Hema Hema」意為「很久很久以前」,這是任何故事最傳統也最古老的開頭,但導演並不採用傳統的敘述方式,而是留下許多曖昧的空白,正如同無語的森林一般,電影展示自身,至於剩下的,就必須由觀眾自行探索了。
故事劇情:9
氣氛營造:10
演技表現:9
題材鮮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