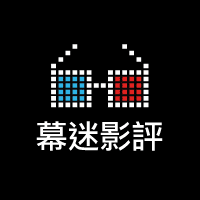電影《邊境奇譚》改編自《血色入侵》(Let the Right One In)原著作者John Ajvide Lindqvist的同名小說《Gräns(Border)》,由丹麥導演Ali Abbasi執導,在2018年代表瑞典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更拿下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最佳影片獎項。
電影第一幕映入眼簾的是巨大的輪船和港口。面容醜陋的女海關Tina擁有異於常人的嗅覺,能嗅出羞恥、憤怒和所有人類極欲掩飾的情感。在一次值勤時她嗅出了旅客手機裡藏有大量兒童色情影片的案件,並遇到了另一個長相和她極其相似的神祕男旅客Vore,偵破案件的同時她也逐漸開啟了自己未知的感官和知覺……

《邊境奇譚》像一則在睡前驚擾孩童的異色童話,北歐精靈巨怪Troll的原形、亦人亦獸的傾頹面孔咀嚼著生蛆的畫面都如床榻邊的黑影般揮之不去。Ali Abbasi將整座雨後氤氳竄出土鏽味和濕氣的森林捧到觀眾的鼻間,我們透過Tina犬類般誇張抽動的上唇和鼻翼,任由嗅覺霧中爬行過自然和情慾,在視覺取向的電影建構另一層次的凹凸地景。

我深愛著《邊境奇譚》對感官異類而生猛的碰觸。
Tina和Vore像兩隻招呼的獸緊貼著、劇烈的抽動鼻翼,恍若回到萬物之始的接吻,既粗暴又柔情的,下顎對下顎交互啃咬、舔拭著彼此臉龐,誠懇的承接溫熱的汗腺和唾液。
雷雨時他們用同樣嬰孩般脆弱的姿勢抱頭蜷縮,那對被閃電追逐(chased by lightning)的恐慌源自於斯堪地那維亞古老的異教信仰,索爾(Thor)會用他的雷神之槌來擊殺巨人,也衍生出後來Troll對打雷懼怕的民間傳說。
於是Tina和Vore看到彼此身上雷擊的傷痕便是種見證,在名字和語言之外,那麼分毫不差。
他們都笑得露出了垢黃歪斜的牙齒。
太陽出來他們便裸身奔跑、嚎叫,在湖邊放聲做愛。Tina的下體發芽式的長出男性的陰莖,對應著Vore不斷生殖產子,如大海一般「恆久受孕的雌性」(Eternal Mother)〔註1〕。男體和女體在對調的性徵裡創造出一種全新的「完整」,一種奇想又陌生的生命樣態—大自然竟在同一個軀體上展演了一個嵌合的生態,美麗又令人費解。〔註2〕

電影後段,Tina終於心痛的發現了Vore是兒童色情案件的幕後主使。
「人類是寄生蟲,為了自娛什麼都不放過。我是幫他們傷害自己。我想讓他們感受到我們的痛苦。」Vore為了報復人類對他族群的壓迫,用自己產下的妖精孩子調換人類嬰兒,並販賣人類嬰兒給戀童癖者去拍攝性侵影片。
電影裡「調換兒」(Changeling)橋段或許觀眾初看並不熟悉,但它在中世紀文學裡十分常見,源自於民俗傳說中精靈、山怪用自己的後代調包人類嬰孩,有時是為了讓人類和妖精的種族繁衍出新的血統,有時正如Vore,只是純粹的惡意。
而電影裡「兒童性侵害集團」(Paedophile ring)的次情節其實並沒有在原著小說出現,這樣的配置或許是向原著作者John Ajvide Lindqvist之前的小說《血色入侵》(Let the Right One In)致意,該小說包含的戀童癖情節在改編後的同名電影裡被刪剪掉了。但我仍認為以戀童癖貫串整部電影顯得突兀,這樣的取材也沒有從事件本身(戀童癖這個舉動)推進對「邊界」(Border)更深刻的討論。

「我不想傷害人,這種想法有人性嗎?」
Tina所有的自我解構、混淆,歸於一個開放性的質問—在這個質問裡她超越了「族群」而以「個體」去回應這個世界,該掌握的只有對每個事件的選擇,而不是對人類邊界無止盡的選邊和分化。
電影最後,Tina收到了芬蘭族人送來的精靈嬰孩包裹,她笑著,拿起甲蟲餵進嬰兒嘴裡,對應到了電影開始時Tina拿起甲蟲卻又放生的畫面。「甲蟲」暗指著她對自然和天性的態度,從愛不釋手卻又因生而為人而捨棄的部分,到她果斷地拿起來哺育新一代的生命—這前後的辯證留給「邊界」(Border)一個曖昧又清晰的可能。
-------------------------------------------------------------------------------
〔註1〕:《海洋》(La Mer),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
〔註2〕:Troll有分為男山妖與女山妖,雖能時男時女變換形貌來戲弄人類,卻並無雌雄同體一說。
.《邊境奇譚》(Gräns),2018年瑞典電影,由Ali Abbasi執導,Eva Melander 和Eero Milonoff主演。
故事劇情:5
氣氛營造:5
演技表現:8
題材鮮度: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