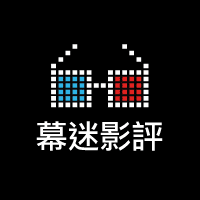兩個薇若妮卡,兩人都有音樂天賦,有相同習慣,母親早逝,跟著父親一起生活,有相同的水晶球,一個住波蘭;一個住法國,冥冥之中互相牽引。
波蘭薇若妮卡因為姑媽生病而前往探望,在當地一場示威遊行中意外被法國薇若妮卡拍到,兩人的生命第一次有了接觸。波蘭薇若妮卡也因為來到此地跟一位朋友通話後,前去參觀音樂演出的排練,卻被指導老師欣賞,最終成為主唱。你還可以發現她爭取到演出機會時,有一位女士坐在台下露出憤怒又不屑的表情,為故事接下來的發展留下伏筆。也就是說,假如波蘭薇若妮卡的姑媽沒有生病,她既不會被法國薇若妮卡拍到,也不會成為這場演出的主唱,整個故事會因此翻轉。
在一次練習中,練唱到一半的波蘭薇若妮卡感到不適,用手指纏繞細繩,勉力唱完。後來,薇若妮卡在路上走到一半,突然感到痛苦,用手摀住胸口,我們才知道她有心臟方面的毛病,她奮力衝到一張長椅上躺下,鏡頭改以她的視角呈現,旋轉90度,有一名男子從遠方走來,張開大衣露出自己的性器,巧妙傳達了生命中的荒謬與無常。
在正式演出當下,波蘭薇若妮卡心臟病發,即使她勉力支撐,仍然不敵病痛,鏡頭改以她的視角呈現,原本搖晃的鏡頭突然天旋地轉,薇若妮卡應聲倒地,鏡頭接著快速晃過觀眾頭頂,宛如靈魂出竅般的視角,下一個鏡頭,變見眾人將土往地下灑在鏡頭上,波蘭薇若妮卡被埋葬了。我們可以發現,整部電影中鏡頭常常切換於拍攝角色特寫以及主角的主觀鏡頭中,而以主觀鏡頭呈現時,鏡頭又頻繁的輕微左右晃動,宛如透過真正雙眼觀看一般。波蘭薇若妮卡的死亡,對電影中的其它角色都是一場悲傷的意外,然而觀眾卻無法以如此單純的視角看待,我想到那位曾以不屑眼神敵視薇若妮卡的女士(也出現在葬禮上),她究竟對此事作何感想呢?替電影增添了複雜的層次。原本以為這樣就結束了,沒想到此位女士日後又在車站與法國薇若妮卡偶遇,她不知道她們是不同的兩個人,原本認為已經去世的竟又出現,你可以同時讀出她臉上的驚訝與愧疚。奇士勞斯基沒有明講這層關係,甚至極容易被觀眾忽略,然而能把如此幽微的人性不露痕跡地放進電影,不管對創作者或觀眾來說,都是挑戰。
波蘭薇若妮卡過世後,法國薇若妮卡無端感到悲傷,甚至放棄歌唱,在學校擔任音樂老師,後來電影主軸轉為法國薇若妮卡與操偶師亞歷山大相識的過程。兩人第一次相遇是薇若妮卡拿著鈴在校園遇見對方,誤以為對方是學校職員而詢問對方關於上課的問題。薇若妮卡在學校偶戲表演時,從鏡中反射才知道他是學校請來表演的操偶師(表演又呼應著波蘭薇若妮卡的死亡),全場都在仔細觀看偶戲表演時,只有她一人盯著鏡子看。後來在上課時薇若妮卡從窗戶望向戶外,剛好看到準備收拾離去的操偶師,她心神不寧得在學校走動,連圍巾拖在地板上都沒注意,接著薇若妮卡又在開車時偶然撞見操偶師,回家時竟告訴父親自己毫無理由的愛上一個不認識的人,觀眾當然知道就是這位操偶師。
沒多久,薇若妮卡收到了一封裝著鞋帶的不署名信封,一開始她感到奇怪而把鞋帶丟進垃圾桶,過一陣子又因為某種莫名的情感跑去撿了回來。後來,她的教師朋友因為感情問題陷入一場法庭糾紛,她一時興起答應為她朋友出庭提供偽證。有一次,兩人在討論時,薇若妮卡問對方記不記得來學校表演的那位操偶師是誰,她想到自己讀給小孩聽的童書內容跟偶戲表演內容很像,拿出童書才知道是同一個人的創作,這時薇若妮卡終於透過童書封面知道他的名字:亞歷山大.法畢。而且童書中還有一個關於鞋帶的小故事(讓人想起那不署名的信封)。薇若妮卡在書店買了一疊這位作者創作的童書,在家中閱讀,我們可以看到薇若妮卡在閱讀的同時,不是用鞋帶纏繞手指,就是用嘴輕咬手指(這是兩個薇若妮卡的共同習慣)。
後來薇若妮卡又收到一不署名的信封,還沒打開就猜中信封中是一個空的雪茄盒(我不禁猜想這是不是童書中出現的另一個故事)。觀眾幾乎確定那兩封不署名的信就是操偶師寄的。此時,薇若妮卡走回家的途中,在樓梯間遇見一名男子,原來就是她的教師朋友訴訟的對象,他質問她為何要出庭提供偽證,她回答不出來,甚至跟他道了歉。你又可以聯想到,若薇若妮卡當初沒有答應她朋友做偽證,她可能永遠不會知道操偶師的身分,此舉造成的間接效果成全了後來薇若妮卡跟操偶師的相見,卻必須以提供偽證做為交換(尤其偽證內容還是要假裝是對方的情人),又將道德的複雜性提升到另一個層次。整部電影充滿不少這樣的巧合,似乎在辯論這究竟是隨機發生的結果又或是宿命的安排,奇士勞斯基的睿智慧黠及生命觀就這樣被隱密藏在電影中,等著細心的觀眾發現。
後來有一次,薇若妮卡回到家中,父親告訴她有一封她的信,打開來是一捲錄音帶,她連去學校都隨身戴著它。錄音帶的內容包括許多環境音、一段音樂還有爆炸聲,別忘了,薇若妮卡之前就曾接過一通用錄音帶播放音樂的電話。薇若妮卡憑著環境音跟郵戳,終於在車站的一家咖啡廳找到操偶師,他正在等她。前面所鋪陳已久的線索終於在此時發酵,他為何要對她提出邀請;她又為何要接受他的呼喚,何況他們還是互不認識的兩人。操偶師說他正在寫一個故事,關於一名女子接受陌生男子召呼喚的故事。薇若妮卡感到難堪與憤怒,你只是為了寫故事而利用我嗎? 她衝出咖啡廳,操偶師追了出去。我們可以發現兩人在咖啡廳進行對話的同時,鏡頭時常切換拍攝窗外被炸毀的汽車,可以理解是奇士勞斯基對當時社會問題的隱喻,但不論是波蘭或是法國薇若妮卡似乎都無視生活中發生的政治、社會事件。
薇若妮卡躲進一間建築物,透過窗戶看著操偶師,他找不到她。這時鏡頭不斷在拍攝薇若妮卡特寫的客觀鏡頭與呈現薇若妮卡視角的主觀鏡頭切換,讓我們得以對比兩人的狀態與神情。薇若妮卡趁著操偶師走遠,跑出建築物攔了一輛計程車,計程車開走,操偶師衝了回來卻追趕不及,我們以為她甩開他了。
薇若妮卡住進一家飯店,房號是287號房(我們想到前一部分波蘭薇若妮卡男友也是住在287號房,又增添了2人間的神祕連結),她拿了鑰匙,一轉身卻撞見操偶師。他們住進同一間房,他說想要多了解她,她把包包裡的東西倒出來給他看,包括水晶球跟底片,我們可以把水晶球當成是兩個薇若妮卡連結的象徵,透過水晶球看出去會形成顛倒的像,電影最開頭及以顛倒與正像呈現了兩地薇若妮卡幼時的樣子。操偶師從底片中發現有波蘭薇若妮卡的照片,拿給她看,法國薇若妮卡第一次親眼看見跟自己互有感應的另一半,忍不住放聲大哭,電影在此時達到了高潮(完全不必依靠戲劇衝突來建立) ,這個舉動完整了整部電影。你可以進一步思考,為何編導安排讓操偶師發現那張底片而不是法國薇若妮卡本人,她是她生命中連繫在一塊卻無緣見面的人;他則是她生命中命中注定相見的人。
操偶師以薇若妮卡的故事創作了新的偶戲:「兩個人同時出生在不同地方,其中一人被火燙傷了,另一人也把手伸向火爐,卻及時收手,並不知道會被燙傷。」他終究還是利用了她的生命經驗,而法國薇若妮卡因此惶恐的離去。電影在此時進入尾聲,薇若妮卡開著車子回到父親的家,鏡頭切換到她在室內的父親,再回到薇若妮卡身上,她打開車窗摸著窗外的樹,電影就此結束。根據奇士勞斯基本人的說法,對歐洲人來說,回到親人的家代表著某種價值,這種價值存在於傳統、歷史與文化中。
奇士勞斯基在拍攝兩個薇若妮卡相互牽引的狀態時很有一手,絲毫不匠氣。你還可以發現,兩人都曾透過窗戶往外看見一名老婆婆,除了長相、習慣,兩人似乎連生命經驗都是共享的。然而編導又將兩人做出對比,強調在個體上的差異,波蘭薇若妮卡一開始就在大雨下高歌,即使其它人都閃躲了,她還是繼續留在大雨下,而且她明明知到自己有心臟問題,卻還是努力爭取演唱機會,充分展現她的熱情,跟法國薇若妮卡做出對比。或許也能理解為,法國薇若妮卡是因為受到波蘭薇若妮卡失去生命的警惕,而選擇了另一種生活方式。
很難說清楚這部電影到底要表達什麼,但是它的通透與細膩,足以感染每位觀者的靈魂。片中大量出現從玻璃、鏡子、水晶球看出去或是反射與折射的影像,也呼應了角色的心理狀態。這部電影所隱含與隱藏的,並非光從劇情上就能體會,雖然它連劇情也不易理解,不過光是欣賞它的攝影、配樂,就是一種享受。當你觀看這部會不斷被世人重新解讀的作品而能稍有體悟時,你怎麼可能不愛上奇士勞斯基。

故事劇情:9
氣氛營造:10
演技表現:10
題材鮮度:9